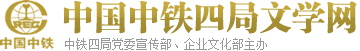二十六、扫地出门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可惜这样和美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红雲打破了。
那是邵松阳病愈上班后的一天,吃饭的时候,秋倩说想参加高考。看红雲不吭声,邵松阳就说:“你高中都没有上,参加高考你能有几成的把握?”红雲随后也说:“你这人就是不长脑子,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就凭你喝的那点墨水,怎么可能会考上,还不是白花钱!”本以为邵松阳和红雲会支持自己参加高等教育考试、进入高校深造,热情鼓励她取得高一级的文凭,想不到他们竟一唱一和地贬低自己,还对自己冷嘲热讽,当面打击她的美好追求和上进心,这使秋倩很伤心。伤心了,就不免抱怨他们当初在自己考上高中的时候却不叫她上,独断地给她填了招工表,让她去了工程队。
“那你是说我们当爹妈的让你早些参加工作反倒错了?”红雲凶巴巴地质问。
秋倩却轻声低语:“我不是那个意思。”
红雲看秋倩不承认,顿时火了,把饭碗往桌子上一蹾:“那是你什么意思!才工作了几天,挣了几个钱,翅膀就硬了!”
红雲越说越气,一甩门进了卧室,从门缝里传出她的“最后通牒”:“家里有一个孩子我就够够的了。你若是嫌我们不好,就滚出去,再也别进这个家!”她撂下这话,等于是要把秋倩扫地出门。
看到秋倩在抹眼泪,邵松阳不但不同情,还指责道:“觉得委屈是吧?我不是说你,这家里就你事儿多,从来不让人消停。”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红雲又与以前一样,对秋倩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不是说三道四,就是指桑骂槐,轻则推推搡搡,重则揪头发、挥拳头。让秋倩更寒心的是邵松阳,不念他在做手术、做化疗期间秋倩对他的照顾,而是卸磨杀驴、落井下石。每逢这个时候,他劝说红雲的少、指责秋倩的多,替秋倩说情的少、任红雲闹腾的多。他虽没有参与殴打,但他时不时地在一旁帮腔、敲边鼓,实则成了红雲刁难、折磨和迫害秋倩的纵容者乃至帮凶。秋瑾呢,只要是替秋倩辩解、说情,红雲还和先前一样,骂她是“吃里爬外的叛徒”、“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秋倩再次感受到了孤单和无助。与以前不同的是,她参加了工作,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工资,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于是,她在部门主任的点拨下,找到行管处分管后勤的副处长,请求在单身宿舍给自己解决一个人铺位,而这个被秋倩叫做“文伯伯”的副处长,先前与红雲、邵松阳同在一个工程段,现在又是邵松阳的下级,对秋倩在家里的遭遇一清二楚,并为此曾善意地劝说邵松阳“注意影响”,但邵松阳总是把责任和过错推给红雲,说是“遇到这样的老婆我也无能为力”,甚至红着脸说“你总不能让我与她离婚吧”。面对秋倩的一双泪眼,这位副处长表示“十分同情”,却又明确对秋倩讲“我不能迈过你爸爸这道坎”,最后答应找个时间“与你爸爸这位好兄弟掏心窝儿地谈一谈”,让秋倩回去“再委屈几天。”
这位文伯伯与邵松阳——他的老同事、好兄弟是什么时间谈的、谈的过程如何,发生没发生争执,秋倩不得而知,她只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天后她接到单身宿舍管理员打给她的电话,说是她给文副处长打的报告已经批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了房间和床位,她随时可以搬进去住。
离开了这样的父母,离开了这样的家庭,对秋倩来说非但没有惋惜和心酸,反倒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她从此远离了刁难和折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解脱。身边没有了凶煞般的威吓,耳边没有了母狮般的吼叫,去掉了身上的重负和心灵的压抑,秋倩又像是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仿佛一只出笼的小鸟,可以在广袤的大地和辽阔和天空自由地飞翔了。她白天在单位里上班,晚上在宿舍里自学,星期天就到市电大办的一个辅导班听课,半年后参加全国统一的高等院校考试,最终被湖南的一所铁路工程财经学院录取。九月初,她步入向往已久的大学殿堂,实现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
在大学里,秋倩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自己在父母身边的悲惨遭遇,而是学着渐渐地淡忘这一切,同时也盼望着父母能有所觉醒和悔悟,回归善良本性,重拥父母之爱,善待她和姐姐妹妹,与其他家庭一样和睦相处,真情相爱,同享天价之乐。
大四最后一个学年开学不久,学校召开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依照往常的惯例,这样的运动会,学校对临近毕业的班级不作硬性规定,以便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或搜集资料、按照导师的要求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或到企业厂矿实习、联系将来工作的单位。秋倩自认不是一个天才,记忆力也不如别人,但懂得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道理,她早早地就开始着手选题,并在指导老师审查同意后,提前准备相关资料。她从学校图书馆里查找图书所用的卡片受到启发,买了几张较厚的牛皮纸,裁切后自行设计制作成一张张抄录资料的小卡片。一天,她吃过晚饭,便背上书包来到图书馆,借了三本相关书籍,走到资料室一个僻静的角落,埋头查找和抄录资料。她是那样地专心,以至于同学孙姗姗坐到了她的对面都没有察觉。孙姗姗看到秋倩没有抬头,就故意地把座椅摆弄出响声,招惹得正在看书的同学们都把惊悚和不满目光投向她,唯独秋倩还是没有理会这一切。孙姗姗赌气地把一封信往秋倩面前一丢,转身离开了资料室。等到秋倩醒悟过来抬起头,只看到了孙姗姗飘然而去的背影。
秋倩一看信封上字迹,就知道是自己原工作单位一个师姐沈小晨介绍的男朋友寄来的,心里便有点慌乱,连忙夹进了一本书里,生怕别人看见。
原来,放了暑假回到单位时,秋倩依原先的相约找到师姐沈小晨,沈小晨给她介绍了一个新调入的同事,并安排他们俩见了一面。这个人就是张琳。
那还是在放暑假之前,沈小晨通过铁路内部线路给秋倩打过一个电话,问了她一些个人情况,在确认她还没有谈朋友后就告诉她:“我们单位新调进了一个大学生,名字叫张琳,原籍是河南,但却在高中毕业后赶上了最后一拨儿‘上山下乡’,被下放到了大西北。国家恢复高考,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北华文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曾在当地的一所党校担任过理论教员。据说,张琳有个姐姐在我们局的一个工程处工作。也就是这个原因,张琳调进了我们局。本来他是要调到局技工学校当老师的,当时,报社的一个编辑因为与妻子长期分居又无法把妻子调过来,只好调回了老家,报社就向局党委打报告要求补充人员。局党委分管报社的领导看了从原单位寄转过来的张琳的档案资料,认为是个合适的人选,就通知人事部门改变原来的决定,对已经来局报到的张琳重新分配工作。就这样,他就到了报社。小伙子来了两个多月了,我打听到他还没有对象,而且人很厚道,事业心也强,还是党员,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年龄嘛,好像比你大个两三岁,如果你觉得行,就请假回来见上一面。”这个师姐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秋倩根本没有机会插嘴,只是在临挂断电话时说了三个字:“那好吧”。
这个师姐叫沈小晨,秋倩调到印刷厂时两人曾同在一个车间,性格开朗直率,人也比较争强好胜,干工作喜欢抢第一,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很得领导赏识。后来调到局行政办公室下的信访室。当时处于“文革”后期,全国统一高考还没有实行,或者说这一制度在“文革”中被废除了,要进入大学深造,就得由各条战线、各个单位推荐,如果被批准了,也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上大学。沈小晨赶上了这个机会,成了一名与后来参加正规高考而毕业的大学生不同、被社会之称为“工农兵学员”。她是铁路职工的子女,其父亲与邵松阳同在一个工程处,后来与邵松阳一前一后调入局机关,而且都在党群口,只不过沈小晨的父亲又在劳资处干了七八年,到退休也还是一个科级干部。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沈小晨对秋倩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也很同情秋倩的遭遇,平时没少帮助秋倩,还鼓励秋倩自学成才。秋倩后来能考上大学,有她自己发自内心在逆境中崛起的决心,同时也是与这位师姐的榜样作用及其不断引导和鼓励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秋倩对这位师姐既感激又尊敬,对师姐的话也听从。
进入十月下旬的淝城,早晚虽有些凉意,但中午还是暖和的,只穿一件长袖衬衣即可,如果行走得急一点还会头上冒汗。铁路子弟学校大操场周围,枝叶密扎的针叶松、钻天杨昂首挺拔,像一排值守道口的职工,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此时正是“月上柳梢头”,秋倩晚饭后在单身宿舍待了一会儿,看窗外天幕朦胧,就按照师姐的提示和叮嘱来到操场的西南角,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在那里徘徊。不用说,这个人应该就是张琳了。
回到学校几天了,秋倩还在想,这个张琳个头中等,相貌平平,身材不胖不瘦,但却有点儿黑,帅气谈不上,但还过得去,如果碰不到更好的,这个人可以考虑考虑。也就是她似想非想、犹豫不决的时候,张琳的信来了。此时,秋倩很想知道张琳在信里说了什么,就顾不得去追上姗姗道个歉,赶忙假装上厕所,就着昏黄的灯光看起张琳的信来。
这是第一次接到“准男朋友”的信,也就是别人说的“情书”。当看到信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倩”时,她的心还真“嘭嘭嘭”地加快了跳动。张琳在信中首先对自己到九江采访、没有给她及时写信而道歉,接着列举了自己的八大缺点。秋倩听说过,谈对象时期,对方写信都是夸女朋友漂亮、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还真没有见过竟在第一封信里说了自己一大堆缺点的,这让秋倩觉得张琳这个人不一般,也令她对张琳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