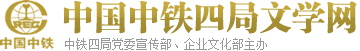十四、电话“通牒”
大女儿秋玲出生后,一向争胜要强的红雲,觉得在第一胎都是男孩的两个姐姐面前矮了半头,脸上无光,熬过满月后,就把女儿送到了宁海的婆婆家。秋玲在农村一直到读完高中,遇到了招工的机会,才到红雲所在的铁路建筑企业下属一个单位参加了工作。
邵松阳的老家说是在宁海市,其实是宁海的郊区,距离市中心还有二十几公里的路程。名义上是郊区,其实就是农村,并不吃商品粮,所谓的区别就是离城市近一些,进城方便一些。邵松阳兄弟姐妹六个,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上学交学费从来就没有一次交齐过,总是会拖上十天个把月。邵松阳高中毕业那年,在东南沿海修战备线的一个铁路建筑单位在当地招收一批铁路工人,父亲让他去报名,他在招工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填的是贫农,“政治面貌”一栏填的是团员。就因为他“根正苗红”,很容易地就通过了“政审”。检查身体时,奶奶抚摸着邵松阳的头说,你一个农村长大的娃,平时吃的都是粗粮,从小没病没灾,身体壮得像头牛,我这几天一直给菩萨烧香磕头,好运一定会降临到我孙子头上的。后来,邵松阳就真的被录取了,走出了他并不热爱的那个臭水沟环绕和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粪便横流的小村庄。
把秋玲送到老家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解放了二十多年,老家的面貌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给邵松阳的印象还是不好,平时也就懒得回家,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家里寄去三块五块的作为女儿的生活费,换句话也可以说是对家里人照看自己女儿的一种补偿。有时候邵松阳或红雲回去了,大多是因为出差路过,每次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还没有与女儿相处熟悉就又走了。与二女儿秋倩、三女儿秋瑾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就是在这看望女儿次数并不多、停留也不长的时间里,红雲也会为家里的琐事或女儿的不顺从而与家人发生争吵,几乎次次都是不欢而散。所以,无论是父女之间还是母女之间,无论是哪个女儿成家之后或女儿们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相互之间都显得很生分,彼此之间的来往也从来没有常态化。后来,他们老两口虽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却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应该认识到的程度,或者说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做法。于是,这种生分将无法削减,裂痕不会消除,隔阂还会延续下去。
秋瑾的话勾起了红雲对往事的回忆。她觉得,无论怎么样,自己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三秋瑾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她越想越生气,抓起电话就拨出了号码。
参加了一个应酬活动的张琳刚进家门,就听到了电话铃声。他穿上拖鞋奔过去抓起了电话:“喂,请问您找谁?”
“啊,是张琳呀,我找秋倩说个事。”
“是妈呀,她就来。”
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的秋倩走来,一个“妈”字还没叫出口,只听听筒里响起了老太太近乎歇斯底里的高分贝:“秋倩,你给我听好了,我没有养你们,但我生了你们,你们就该管我。我知道我将来的下场,我得攒些钱准备将来为我自己养老。邵松阳是你们的爹,今后我可不管了,你们去管吧!”声音到此戛然而止,听得秋倩一头雾水。她猜想着这里面肯定有原因,就把电话打向秋玲。秋玲的电话传来忙音。再拨,还是忙音。她只好又打秋瑾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