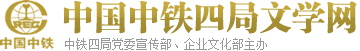二十二、“老皮”师傅
与秋倩同一批的知青,全局有四五百名,属于局机关的有三十来人,按照异地安排的原则,他们大多被分配到了地处芜湖的第九工程处(简称九处),而九处又把他们安排到了参与皖赣铁路施工的基层单位。就这样,秋倩来到了地处皖南山区的祁门。
祁门当时是屯溪市的一个县,为徽州六县之一,也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它位于安徽省的最南端,与江西省交界,建县于唐永泰二年,因城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门而得名。祁门是安徽省林业重点县,又是祁门红茶、凫峰绿茶的主要产地,到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正在修筑的皖赣铁路就穿行在这似诗如画般的风景之中。
皖赣铁路穿越安徽江西两省,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其建设从设计蓝图到开通运营,几经修改、建建停停,前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1905年7月,清朝政府开始修建由芜湖至景德镇的皖赣铁路,仅仅完成芜湖至湾沚的32公里路基和桥涵便草草收场。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由江南铁路公司负责修建芜湖至孙家埠路段,工程未完便停止了。1936年7月至1937年10月,京汉铁路工程局先后修建了安徽和江西两省境内的三个路段,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再次中断了建设。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寇南下,下令拆除已经铺设的钢轨,破坏现有的路基和桥涵,留下支离破碎的废墟横卧在江南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即把重新修建皖赣铁路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1958年9月至1961年7月先后两次开建,时间不长便因经济困难而停止修建。1971年至1973年,南昌铁路局管段自建通车,安徽省境内则由安徽省组建皖赣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各地、县相应成立指挥部,组织民兵和部分专业队伍投入施工。不久,由于国家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安徽省皖赣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被撤销,民兵返乡、专业队伍息工,皖赣线再次停建。
1973年,交通部(铁道部已并入)决定,将皖赣铁路芜湖至景德镇段的修建任务交给铁道建筑第四局施工。为了保证及时开工,经四局与武汉军区设在该局的军管会共同研究决定,全线施工队伍投入三个工程处,由物资供应处负责提供工程所需的各种物资,并成立“铁道建筑第四局皖赣铁路建设指挥部”。三个工程处分别为五处和从昆明铁路局划归进来的四处、九处,物资供应处则在宣城设立“皖赣铁路物资供应站”,这个供应站在施工沿线设立了三个工地材料厂,而红雲就在郭溪工地材料厂工作。1974年7月1日,皖赣铁路建设再次上马。开工不到一年,由于国家压缩投资规模,施工所需要的钢材、水泥、木材等供应不足,四局只好削减施工队伍,停止隧道桥梁等重大工程项目,留下部分人员肩负起路基土石方的施工任务。1975年,负责北段施工任务的四处被调往河北静海,参加津浦铁路北段改造工程建设,五处调往九江,为上马大(冶)沙(河街)铁路做准备,留下的任务就由九处一个单位承担。从此,皖赣铁路线、桥、隧齐头并进的施工格局被打破,施工进度明显缓慢了下来。1975年10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秩序的主张,力图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个“四人帮”团伙视邓小平为眼有钉、肉中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掀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此时的九处造反派也活跃起来,上蹿下跳,到处串联,把邓小平的一系列排除干扰、发展经济的言论搜集起来汇编成册,作为揭批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反面教材,到处煽风点火,批斗敢于抓生产的干部,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使全处的施工生产基本陷于停工状态。
1976年10月,叶剑英等一批老将军发挥运用自己的睿与智威望,鼓动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将“四人帮”抓进了牢房,全国人民无不为“十月的胜利”而欢欣鼓舞。随后,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着手拨乱反正,全国各地开始纠正冤假错案,同时对“三种人”——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进行清理,这些人或造反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或拉帮结派、诬陷迫害干部群众,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或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对社会危害极大,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给党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对这三种人,除明确悔改者外,原则上都要开除出党。为了清理和处理九处的造反派,使一度瘫痪的九处重新振作起来,中共安徽省委向铁道建筑第四局派出联络组,会同四局的工作组,以举办学习班的形式,把近200名造反派的骨干分子集中起来,用三个月时间进行学习和洗脑。邵松阳被局党委任命为工作组的副组长参与了这项工作,并由他制订学习计划,安排作息时间表,指定局党校的理论教员,组织当年的造反派们成员封闭学习,写出材料,分清是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进行人人过关,对个别错误严重、影响极坏的造反派骨干给予处分,剩余的人员在写出局面材料包括保证书后,分别调往其他工程处另行分配工作。与此同时,把造反人员集中的部门和派性严重的工程队打散,然后像掺沙子似的分到各个单位,并对九处及所属工程段的领导班子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至此,在全局发生动乱最严重、先后持续了十年的九处,终于重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齐心协力奔小康的目标指引下,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皖赣铁路建设再次获得了新生,参与施工的单位在铁道建筑第四局党委和行政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在全线掀起了大干高潮。为了增强施工生产能力,四局在加大机械设备投入的同时,也在人力上给予较大幅度的补充,途径之一就是从全局职工子弟中招收了一批知青工,其中相当一部分上了皖赣线工地,秋倩就是其中的一员。经过两天简单的安全技术培训后,这批知青工被编入了各工班,秋倩所在的班为综合二班,主要是配合机械化施工队伍,进行路基土石方开挖和铺轨后的上道砟作业。
铁路施工单位职工的驻地一般都远离村庄,据说这是从老铁道兵那里延续下来的传统,一来不打扰当地的百姓,二来减少与村民的接触、摩擦和矛盾,三来也便于对职工队伍以及家属的管理。秋倩所在的工程队也不例外,沿袭了这一做法,把职工驻地建在了一个小山包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队长用铁棒敲响食堂门前挂着的一截钢轨,那就是发出了出工或开会的“命令”。每天到工地去干活,出了驻地前方搭建的彩门,最远距离还需要走大约三四十分钟的路程。负责带秋倩和另外两名知青工的师傅叫裴宝成,是甘肃定西人,其姓的读音在普通话里为“赔”,可甘肃当地却与“皮”相同,所以他的老乡都喊他“老皮”。一天上午,秋倩在工间休息时叫他“裴师傅”,他竟不知道是叫他,直到秋倩向他招手,他才明白了过来。秋倩问他,工地上流传的“皖赣‘晚干’,停停建建;修了几十年,不见车轮转”是怎么回事?裴师傅就把班里的青工叫过来,让大家围成个小圈,给他们讲述皖赣铁路六下六上的大致经过,最后还说,“皖赣‘晚干’,停停建建;修了几十年,不见车轮转”这18个字,概括了皖赣铁路修建的坎坷经历,既包含着安徽江西两省人民的希望和期盼,也渗透了建设者们半个多世纪的苦辣酸甜。
当时,全国都在宣传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实行包干到户的做法,并作为承包的典型加以推广。在皖赣线建设中,施工班组虽没有进行单独核算,但开始对每日计划完成的任务进行定量,然后分配到人,谁先完成谁可以先收工,如果不回去休息而接着干,领导知道了,虽不会给予物质方面的奖励,但会以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在职工大会上加以表扬。秋倩这个班主要负责对推土机平整出的路基边坡进行平整、刷齐,缺土的地方就推些土过去填平。班长给每个职工划分一段,几个身强力壮的男职工总是先完成,而落后的大多为秋倩她们几个女青工。先完成的那些人心中充满自豪感,他们把铁锹、推车放进工具棚里,然后或唱着《打靶归来》之类的歌、或嬉笑打闹着返回驻地,而没有完成的就会长长地叹一口气,自愧弗如,然后泄气地坐在地上。当然,有时候,她们也会不服气地鼓一把劲,加快作业速度,直到完成自己的那份任务。裴师傅这人很厚道,即使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也不走,而是经常走过来给女青工们帮忙。看到秋倩身体单薄,动作笨拙,铲土、推车那样吃力,裴师傅就猜想:秋倩这女娃矜持、稳重,让人感到比较有修养,不是一般职工的子弟,倒像个大家闺秀。一天收工后,走在回驻地的路上,裴师傅关切地问秋倩:“听说你们这些知青都是从局机关下来的,你也是?”看到秋倩点点头,就又问:“来工地之前没有干过体力活吧,你爸爸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吧?”这次秋倩转过头看了一眼他,却不愿把父母的真实身份告诉别人,也不想用他们的职位和头上的光环照亮自己,就回答道:“我爸是烧锅炉的,我推过煤。”裴师傅摇摇头,表示不太相信,但看到秋倩认真的样子,只是“哦”了一声,就把话题岔开了。
在一同来工地的知青中,秋倩与屈水红的关系比较密切,虽住在一个宿舍,但因为不在一个班,干活的时候两人很少在一起,只有晚饭后才能在一块儿说说话、聊聊天。屈水红的父亲是局经营计划处的一名科长,母亲是局直属医院内科的一名医生。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就她是女孩儿,所以在家里属于宝贝疙瘩,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她来封信。所以,每个月到了该来信的日子,屈水红收工后就会到队部的传达室看一下。如果拿到了信,屈水红就显得很兴奋,还会把信中的内容说给秋倩听。每逢这个时候,秋倩就会有意识地躲开,以免屈水红所享受的父爱和母爱触痛自己受伤的心灵。
那时,全局每个处都有一个电影队,巡回到各个工地放映电影,以活跃施工现场的文化生活,鼓舞参战职工的士气。一天,队部来了处里的电影队,说是要放映朝鲜的宽银幕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队长特意宣布:提前半小时,下午五点半收工。
放映场地就在队部食堂前每天早点名的场地上。在此之前,秋倩曾听说过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所以,当看到小女儿顺姬被地主婆推倒,旁边热火上熬的参汤和着炉灰全掀到了顺姬的眼睛里,顺姬从此成了瞎子时,秋倩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当放映到花妮发现顺姬偷偷在街头卖唱赚钱、又气又怨又心疼的场面,当看到花妮和顺姬好不容易买到了给妈妈治病的药,高高兴兴地回家,却发现妈妈已经撒手人寰时,当看到顺姬每日在村口的山岗上哭喊话着“妈妈”和“姐姐”时,当听到影片中反复吟唱“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卖了花儿,换来药呦,治好生病的好妈妈:卖花来呦,卖花来呦,快快来买这束花。让这鲜花和那春光洒满痛苦的胸怀”时,秋倩更是与影片中的花妮、顺姬、哲勇一样,时而伤心,时而悲痛,时而愤怒。之后连续几天,秋倩都不能从电影的情节中解脱出来,一有空闲就会沉浸在爱与恨、痛与伤的纠结之中。晚饭后看不见秋倩的身影,屈水红就猜想,秋倩一定是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偷偷地抹眼泪。
屈水红猜得没错。驻地背后约1000米处有一条溪流,水是从远处大山里流过来的,平时水量小,深的地方也不及腰部,但到夏天涨水的时候,晚上睡觉都能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有些个男职工经不住诱惑,时不时地从驻地偷偷溜出去下水游泳和洗澡,如果被队领导知道了,轻则叫到办公室骂一顿,重则会在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并勒令写出书面检查将至队部。
时下已是晚秋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午后干活会出汗,但到了晚上就得穿秋衣和外套,所以职工基本上都不会走出宿舍了,男职工们喜欢打打牌、下下棋,女职工则愿意织袜子、打毛衣。此时此刻,秋倩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双手托腮,望着东方升起的一轮明月发呆。她本来是要把自己的过去深埋在心底的,但看了《卖花姑娘》,又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特别想念远在济水的姥爷、姥姥、二姨妈和鲁钦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