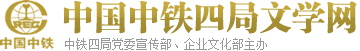二十八、校园献吻
张琳的来信,使秋倩的心中泛起了层层涟漪,一个少女的春心不由地荡漾起来。她回忆起与张琳第一次约会的情景,再看看信中所列举的八个缺点,感觉到这八个缺点不仅不是缺点,反倒是他的优点。在表现欲正处于强烈的时期,一个男孩子能如此地直率和坦荡,实在是难得。由此,他对张琳开始产生好感,并决定与他交往下去。于是,秋倩给张琳写了一封回信。
从此以后,只要张琳来信,她就很快地写一封回信,后来她也觉得哪个环节有点不妥。仔细一想,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她暗暗惊奇:每次把信发出去,自己便数着日子地等着、盼着张琳回信;而一旦收到张琳的来信,自己又按捺不住心中涌起的倾诉,迫不及待地给他写回信。她为这种惊奇的发现而心儿猛跳、脸上发烧,悄悄地问自己:秋倩呀秋倩,你怎么比一个男孩子还着急,好像自己嫁不去似的。你这么不矜持,哪还有点闺中少女的稳重与内秀,真没出息。她也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不能头脑发热,要用时间来检验张琳是否真心实意。
自从与秋倩交往后,张琳也摸出了一条规律,只要他给秋倩写信,那么,不出一周,秋倩肯定就会有回信,而且信中的话语处处流露出关心、理解、体贴,饱含着一个怀春少女的温柔。就这样,张琳和秋倩之间鸿雁传书,渐渐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步步加深了相互的感情。虽说各自在信中没有直白地写出“爱你”、“吻你”、“想你想得我睡不着觉”之类黏黏糊糊的词语,但透过字里行间,双方都能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那份关心和牵挂,能触摸到对方开阔的胸襟和温暖的情怀,能体会并享受到远方恋人所爱和自己被爱的心灵。
当张琳寄出第21封信时,已经是1988年初春的季节,高大的玉兰树新芽绽露,白花盛开,道路两边杨柳依依,几户居民在房前屋后开垦的小菜园子里,向阳一面的油菜花吐出一串串金黄,招惹得一群群小蜜蜂嗡嗡飞来,在花朵间忙碌地采蜜。张琳的心中也和这阳光灿烂的春天一样,暖意充盈,畅快甜蜜。就在他把刚写的信投入邮筒的时候,他就盘算着什么时间能收到秋倩的回信,巴望着早日看到她如人的字迹。
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听到负责收发报纸、信件和文件的资料室邝老师那声“小张,你的信”的呼唤。坐在办公桌前,张琳感到墙上挂钟的指针走得像蚂蚁爬;回到宿舍,本来是自己很喜欢看的书,却看不了几页就坐不住了,屁股下面像是有小石子硌;到了周末,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煎熬了,张琳就走进了沈小晨的办公室。沈小晨正在登记稿件,看到他进来就招呼了一声:“是小张啊,你坐。”然后放下手中的笔,问道:“你看我这几天老在跑我家小孩学习的事,也没有顾上问,你与秋倩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张琳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几乎就要掉下来了。沈小晨见状,连忙走过来安抚他:“你这是咋地了,和秋倩闹矛盾了,快给我说说。”
张琳见沈大姐误会了,连忙解释道:“没有没有,就是她十多天没有来信了,我心里有点急。按说她早就该收到我的信了呀。”
“你这人也真是,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沈小晨嗔怪道,然后把他按到椅子上坐下,却又拉他站起来,说:“你先到你办公室等着,我这就去大楼给秋倩打个铁路长途,别着急啊。”
这个局是铁道部下属的基建单位,内部电话联系都采用铁路专用电话线路,沈小晨说的大楼就是局机关的办公大楼,位于报社的北面,距报社不足五百米,重要的管理职能部门都安排在里面,局领导和个别核心部门的电话可以向铁道部和各个铁路局以及省外其他铁路单位直拨。
打完电话,沈小晨就往回返,路上见了熟人,也嘴上打招呼,脚步却没有停下来,匆匆忙忙地回到报社,向张琳转达与秋倩通话的内容。原来,秋倩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忙着准备毕业论文,经常在图书馆忙到闭馆才回宿舍,睡眠严重不足,加上她上学的所有开支都是她每月二十来块钱的工资,再紧巴也从来不向邵松阳和红雲张口要,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省吃俭用,营养跟不上,她又有低血糖,所以在一天早晨端着脸盆到楼下洗漱时,一阵头晕使她站立不住,连人带洗漱用具叽里咣当地摔下了楼梯,被同学背到了校医院,所幸的是没有伤着骨头和内脏。一听这些情况,张琳心急如焚,却又六神无主。还是沈小晨给他出意,让他向报社总编说明情况。总编一听张琳与局机关领导的女儿谈对象,心想,可不能在自己手里坏了这等好事!他想了片刻,很快给张琳在湖南安排了一项采访任务,让张琳公私兼顾,别人也提不出异议和意见。就这样,张琳持一张单位开具的铁路免票,坐上了从淝城绕道上海最终开往株洲的列车。
这是张琳第一次到位于中南腹地的株洲。秋倩说过,她所在的学校距市中心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需要坐公交车。出了火车站,张琳茫然了:究竟是坐几路车,需要不需要转车,要转几次车,他对这些一无所知。好在他经常外出采访,寻道问路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各地人所说的方言,虽然他说的不地道,但当地人说的话他都能听得懂。比如普通话说“湖南”,当地人说成“斧兰”;说“头”,河南人叫“低脑”,而四川人叫“脑壳”,等等。
张琳首先打听开往铁路工程财经学院应该坐几路车、从哪个车站上车,上车后再向售票员询问需不需要倒车、要倒几路车、在哪里倒车以及在哪里下车,就这样一边行进一边打听,没费什么周折便走进了这所大学的校园、来到秋倩所说的财会系宿舍楼门前。
听到同学“秋倩,秋倩,有记者找你”的喊声,秋倩还感觉纳闷:我在市里没有熟人,也不认识什么记者啊,找错人了吧?等她来到门口,只见张琳正在向楼里探头张望,惊喜之中她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琳,怎么会是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走在楼道里,秋倩悄声嗔怪张琳:“我还以为是省报市台的大记者呢,原来是本局的小报记者,够张扬的!”
张琳解释:“还不是你们学校的门卫要我拿出证件登记,这不就亮出了我的身份嘛!”
宿舍里的同学见秋倩领着个戴眼镜的男生进来,对秋倩介绍“这是我单位的同事”的话半信半疑,礼貌性地与张琳寒暄了几句,就相互挤眉弄眼地说笑着走了出去。
那天师姐沈小晨打来电话,秋倩刚从医院出来回到宿舍,没有到教室上课,是系办公室把电话转到了宿舍值班室。现在张琳又问起,她只好述说了自己摔伤的过程,对张琳的询问回答得轻描淡写。她是不想让张琳过多地担惊受怕,可张琳却不放心,仔细地察看着秋倩的头部、脸面,还要秋倩捋起袖子察看胳膊和肘,在确认真的没有大碍之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学校里没有招待所,秋倩领张琳在学校的学生食堂吃了晚饭后,要送张琳到市里住宿,张琳问:“那你呢,也在市里住?”看到秋倩朝他瞪眼,张琳的脸立即红了,赶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秋倩不依他:“那你是这个意思?”张琳更蒙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看到张琳迷惘的傻样,秋倩觉得他老实得可爱,忍不住笑了起来,张琳这才明白秋倩是在逗他玩,于是抢过去就要胳肢她,秋倩见状连忙摆摆手算是求饶。张琳这才又一本正经地说:“我是说你跟着到市里,天太晚了,哪还有公交车,你怎么回学校!”秋倩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我们有个自习的教室,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人了,反正现在天热,我给你拿张凉席、一个枕头凑合一晚,只是委屈你了。”张琳说得很痛快:“没事儿,不就一晚上吗,我能对付。”当晚,张琳就在教室里过夜。不过,事后想想,他觉得很幸福,因为当天晚上,秋倩陪着他坐了大半夜,两人说得很投机,而且秋倩在离别时答应了他的请求——给了他一个亲吻。
第二天,张琳要去采访,秋倩陪伴张琳到市里,在株洲市中心一个特色湘菜馆请吃饭。张琳说:“我是男同志,应该我来请。”秋倩却批评他有大男子主义,并说她是“地主”,应该听她的,张琳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秋倩问张琳爱吃什么,张琳说:“随便吧。”秋倩就又盯着他问:“‘随便’是道什么菜?”这一次张琳学精了,也调侃她:“这道菜对女士们来说有的爱吃、有的不爱吃,你可爱吃?”秋倩没有张琳见识广,不知道张琳在故意挖坑,还一本正经地说:“我不行。”张琳听罢此言,高兴得拍起了巴掌:“太好了!”看到站在一旁的服务员也跟着他笑,秋倩猜想自己吃了亏,却又不知道亏吃在哪里,于是就不再理他、开始点菜。秋倩点了一盘红烧田螺,一条清蒸白丝鱼,一份香辣黄鳝段,还有一份“小龙三吃”。等饭菜端上来,张琳才知道这几个菜确实有湖南当地的“特色”:田螺大得像乒乓球,白丝鱼则没有去鳞,一份香辣黄鳝,光干辣椒和花椒就占去了一大半,而所谓的小龙其实就是蛇,“三吃”则是把蛇皮与香菜凉拌,蛇肉做成油炸椒盐的,蛇骨则煲了一盆鲜美无比的羹汤。见服务员还端上来两只碗,里面一种红色一种绿色,张琳就指着问:“这是什么东西?”服务员看着他,答非所问:“听口音你是北方人吧?”接着就介绍说:“这只碗里是白酒泡的蛇胆,这只碗里是蛇血。蛇胆可以明目,蛇血可以补肾。”说完又特意看了张琳一眼,微笑着转身而去。看到张琳目瞪口呆,秋倩以为他是被服务员的美貌吸引了,伸出一只手在张琳面前连晃了几下:“嗨,小心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了!”张琳这才回过神来。他知道秋倩是在与他开玩笑,就没有接话,眼睛在两只碗之间来回瞄。秋倩看他有点胆怯,就问他:“你没有喝过吧,敢不敢?”张琳一看秋倩将他的军,笑笑说:“你这是激我吧,我才不上你的当呢。”然后就转移了话题,说:“你点的这几个菜别说吃过,我连见都没见过。”秋倩就笑话他:“真是个土包子。”张琳不介意地笑了笑:“还有比我更土的呢。”
看秋倩纳闷地眨巴眼,张琳就问:“你在湖南也两三年了,湖南也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难道你不知道,在南方,男的不能说‘不行’、女的不能说‘随便’?”秋倩这才明白刚才服务员为什么也跟着笑,就自我解嘲道:“我们在校生哪有你们新闻记者见多识广呀。”
张琳本来还想说“你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但他怕这话伤了秋倩的自尊心,于是就转过话题,讲述了在原单位同事身上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同事姓李,在张琳所在的党校是管总务的。有一次,单位组织教职员工到改革开放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参观考察,回来后领导召开座谈会,让考察团的每一个人谈谈自己的观感,在发言时老李说:“深川的菜就是好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份粉丝,味道真是绝了,就是数量少了点。”他话音刚落,同行的一位教员纠正道:“老李你真土,那可不是粉丝,是鱼刺,几十块钱一份呢。再说,那也不是深川,是深圳。”引得大家好一阵大笑,把老李的脸都笑红了,喃喃地说:“咱没有文化,鱼刺没吃饱,这亏可吃大了。”
秋倩听着,也不禁笑了起来。她劝张琳多吃菜,张琳嘴上说“好好好”,可就是只动筷子却很少夹菜。
原来,张琳出生在河南洛阳东边三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县城,四五岁时曾随母亲到父亲工作的陕西户县生活过一段时间,高中毕业后赶上了最后一拨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远赴大西北的甘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又参加高考到兰州上大学,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北方养成的,而北方人根本就不吃螺蛳、黄鳝、老鳖、青蛙,更别说吃毒蛇、蛤蟆、老鼠之类的了。秋倩虽然小时候在北方,但她上初中时就到了具有南方习惯的淝城,参加工作后到了皖南。上大学期间,她利用在单位和学校享受铁路免票的机会,一到寒假、暑假,都随同班里的同学四处游玩,几乎走遍了中南地区的各个大小城市。她深有感触地告诉张琳:“南方人除了四条腿的板凳不吃,其他带腿带脚带尾巴的都是他们的盘中菜,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一点儿都没错。没有多长时间,全国到处采访的张琳吃遍了各地的风味,那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他也无所不吃,完全被同化成了南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