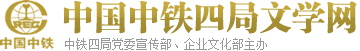三十八、儿子大了
秋倩与婆婆相处机会不多,时间也不长。早在与张琳谈对象时,张琳曾带着她到过老家。后来秋倩有了儿子冬征,婆婆还专门到当时她和张琳居住的单身宿舍来照看过她和孩子。虽说孩子一满月老人就走了,但秋倩还是感到了从济水来到亲生父母身边所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而且自从给张家生了这个宝贝儿子,秋倩更受到公公婆婆的厚爱,每次回到老家,公公婆婆总是支使前来看望他们的女儿干这干那,却从不让秋倩沾手。尤其是婆婆,常常把秋倩拉到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问长问短、说这说那。而公公呢,每当要做饭时,总是询问秋倩:“倩,你想吃什么?”如果是连着吃了两顿面食,下一顿一定会做米饭。回老家多少次了,别说秋倩,就是张琳也没有起床做过早饭或买过早点。张琳的父亲有早起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五点多钟就起床,外出走动走动,打打太极拳、练练太极剑,然后顺便把早点带回来。如果头天有剩下的馒头或烙饼之类,老人就会煮上一锅小米稀饭或玉米糁儿糊糊,再配上香油拌的咸菜丝或拍黄瓜,虽说简单了点,但却具有当地的特色,这让秋倩很感动,常常想起小时候在济水的甜蜜日子,并把这种日子与和邵松阳红雲在一起的日子相比较,感慨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大有云泥之别。
秋倩对自己的父母充满失望,但她对自己的儿子冬征却十分爱怜、充满希望。平时称呼儿子,她很少叫他的学名,连小名也不常叫,总是儿子长儿子短的。特别是对冬征的学习,她平时要求非常严格,家中有事很少让儿子请假,以免耽误他的学业。这次回河南奔丧,秋倩事先接到婆婆生病的消息,敏锐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头。这是因为,平时河南家里来电话都是张琳的二姐打的,这次却出人意料地是二姐夫,而且不是平时捎带一句“没有事儿、甭萦记”,而是特意提醒她“冬征要是能回来也尽量回来一趟”,这让她顿生疑虑。她马上给张琳打去电话,可张琳的电话却长时间处于“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状态。等到与张琳联系上,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当听张琳说他直接从蚌埠回家时,这边已经落实“老人于当天下午四点多去世了”,就决定当晚由大姐夫开车,拉上大姐、秋倩一同到河南。
途中,秋倩想起应该给冬征打一个电话,就从包里拿出手机拨打号码。坐在旁边的大姐说:“太晚了,孩子都睡觉了,明天吧。”秋倩就说:“现在才十一点,他还在教室呢。”正说着,电话通了,一问,冬征果然还在教室里。秋倩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并说“你学业重要,可以不回老家”,但冬征却说:“我耽误的学习时间可以补回来,但如果不回去送奶奶最后一程,机会错过了可是永远也挽不回了。”冬征还说,我回去送奶奶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想陪陪爷爷。爷爷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身体再好也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我要回去陪陪爷爷,哪怕就坐在爷爷旁边,拉住爷爷的手,给他端一碗水,对爷爷也是一种温存和安慰。听到冬征十分坚决的口吻,秋倩突然觉得儿子长大了,懂事了,有他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了。
在为婆婆治丧的日子里,秋倩留意到,冬征几乎在爷爷身旁寸步不离。每到吃饭,冬征先给爷爷把饭菜端到跟前,然后才去盛自己的;看到爷爷吃完了,就慌不迭地接过空碗,惹得老人不知道如何表达对这个孙子的爱怜,时常抚摸着他的头感叹不已。
在办完丧事的第二天,张琳一家三口就乘坐大姐夫的车返回了淝城。
一天,张琳和秋倩参加完一个朋友的聚会回到家,刚打开客厅的电灯,电话立马响了。他们二人并不知道,红雲为邵松阳看病的事闹心好几天了,她需要人帮忙,希望三个女儿中哪怕有一个打电话过来,连等了几天,可就是没有人打来电话,想来想去,远水解不了近渴,离得远的秋玲和秋瑾她也不愿麻烦,于是就想把这个棘手的事情交给秋倩和张琳。所以,吃完晚饭后,她打开电视机,心却不在电视里播出的节目上,而是站在窗户边时不时地眺望对面二女儿的家,但那边却一直没有亮灯,于是只好下楼与小景一同散步去了。等她散完步回到家中,邵松阳坐在沙发上看中央二套重播的《新闻联播》,她就穿过客厅再次向对面张望,只见秋倩家还是黑咕隆咚的,她骂了一句粗话正要转身离开,却见那边的灯亮了,就立即拨通了电话。张琳听到电话铃声,来不及穿上拖鞋,直接奔过去手抓起话筒,刚说了“你好”两个字,就听对方劈头说道:“你爸这几天连续发低烧,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死活也不去,我管不了了,你们来管管吧。”
张琳听出来对方是红雲,觉得应该秋倩来接这个电话,就表明“我是张琳”,还没等他说出“我让秋倩来接电话”,红雲就表现出了不耐烦:“我不管你是谁,反正你们得管。”
听红雲如此说,张琳心里很不爽,但又不便与自己的丈母娘计较,就说:“那我叫秋倩过去一下。”秋倩就在旁边听着,等张琳放下电话,秋倩已经走到了门口。张琳笑着揶揄她:“到底是自己的亲爹新娘,跑得比谁都快。”
秋倩走后,张琳接过秋倩洗了一半的锅碗筷勺,边洗边想,这次买新房,挑来挑去还是离不开他们的视线,就像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他不由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就是天意!”